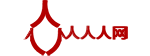保罗·韦纳:历史不是事实,也不是实测平面图,而是情节
如果一切已经发生过的事情都同样值得历史关注,这样的历史难道不会变得一团混乱?一个事件如何比另一个具有更多的重要性?怎么样这一切才最终不会蜕变为各种特殊事件的灰色浮雕画?一个纳韦尔农民的生平也许抵得上路易十四的生平,此刻在大街上响起的汽车喇叭声的价值可能相当于一场世界大战……我们能够逃脱历史主义者的追问吗?历史中必须有一种选择,以避免成为各种特殊性的一盘散沙,也避免一切都不相上下的无所谓态度。
回答是双重的。首先,历史对个体事件的特殊性并不感兴趣,它感兴趣的是它们的特征性;其次,那些事实,如我们就要看到的,并不像很多沙粒那样存在。历史并不是一种原子决定论:它在我们的世界里展开,在那里,一场世界大战确实比一场汽车喇叭的合唱有更多的重要性;除非——一切都有可能——这场合唱本身引发一次世界大战;因为那些“事件”不是以孤立的状态存在的:历史学家发现它们全都组织为一些整体,在其中,它们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原因,目的,机遇,偶然,借口,等等。我们自己的存在状态,毕竟,在我们看来并不像原子的偶然事件的灰色浮雕画;它一开始就有一种意义,我们懂得这种意义;为什么历史学家的处境该是更加晦暗阴郁的?历史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是用同样的材料造就的。
因此,这些事件有一个自然的组织,历史学家发现它是完成的,一旦历史学家选定了他的论题,这个组织就是不可改变的:历史工作的努力就在于重新发现这一组织构造:1914年战争的原因,各参战国的目的,萨拉热窝事件;历史解释的客观性的边界部分地归结于这一事实,每个历史学家都能够或多或少地推进对历史的解释。在所选定的论题内部,事件的这一组织结构,给予它们一种相对的重要性:在一部有关1914年战争的军事史中,对前哨的突然袭击不如有恰当理由占据报纸大幅标题的一场攻势重要;在同一部军事史中,凡尔登要比西班牙流感具有更重要的价值。毫无疑问,在一部人口史中,情况则刚好相反。只是在我们竟敢去追问,凡尔登和西班牙流感,从大写的历史的角度来看,究竟是哪一个绝对更重要的时候,困难也许才开始。也就是说:那些事件不是孤立地存在,而是彼此间有着客观的联系;对一个历史问题的选择是自由的,但是,在被选择的论题之内,诸事实和它们之间的关系保持它们既有的状态,没有什么可以使它们发生任何改变;历史的真相既不是相对的,也不是那样不可接近,像一个从所有角度都无法言说的彼世,像一个“实测平面图”。
情节的观念
各个事件不是孤立地存在着,在此意义上,历史的网状组织就是我们将称之为一种情节的东西,一个非常人性而很少“科学的”由各种质料因、目的和偶然组成的混合物;一句话,历史学家随意切割的生活的一个侧面,在那里,事件有它们的客观联系和它们的相对重要性:封建社会的起源,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政治,或者只是这个政治中的一个插曲,伽利略革命。

情节这个词有个好处,就是更多地让人们想到,历史学家所研究的,跟一部戏剧或者一部小说——《战争与和平》或者《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一样,都是关于人的。这个情节并不一定根据时间的顺序安排:就像一部戏剧里边一样,可以从一个场景推展到另一个;伽利略革命的情节使伽利略与17世纪初物理思想的背景发生冲突,与他模模糊糊在自身感觉到的渴望发生冲突,还有与正在流行的问题及其参考,即柏拉图主义和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冲突,等等。情节因此可以是各种不同的时间节奏的横切面,是光谱分析:它将永远是情节,因为它是人性的,尘世的,因为它不会是决定论的一块碎片。
一个情节不是一种决定论,在那里叫做普鲁士军队的一些原子击溃了叫做奥地利的一些原子;细节因此在那里具有比情节的流畅进展所要求的更多的重要性。如果这些细节由诸多小规模的决定组成,那么,当俾斯麦发出埃姆斯电报,这一电报的作用会以与这位首相的决定同样的客观性得到详细说明,而历史学家可能会从跟我们解释是什么样的生物学程序把这个俾斯麦带到世界上来开始。如果这些细节不具有相对重要性,那么,当拿破仑向他的部队发出一个命令,历史学家可能会每一次解释为什么那些士兵服从他(我们记得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差不多用这些措辞提出过历史的问题)。的确,如果有一次那些士兵没有服从,这个事件也会是合情合理的,因为戏剧的进展可能已经改变了。
那么,到底是哪些事件值得引起历史学家的兴趣呢?一切都要视所选定的情节而定;就事件本身而言,它既不是有趣的,也不是相反。对于一个考古学家来说,去清点萨莫色雷斯的胜利女神翅膀上羽毛的数目是有趣的吗?这样做,将是一种值得尊敬的严谨的表现,还是显示出一种过分多余的精确性?不可能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没有情节的事件什么都不是;它会变成某种东西,如果人们把它作为主人公,或者把它想象为一部艺术史的戏剧,在那里人们让不多渲染笔墨、不精心修饰图案的古典主义潮流,装饰过重且工于细节的巴洛克潮流,以装饰性元素充斥空间的蛮族艺术的趣味,彼此一一相续,轮流登场。
我们注意到,如果我们刚才所说的情节,不是与拿破仑有关的国际政治,而是拿破仑时代的法国军队,它的士气和它的态度,拿破仑近卫军老兵们惯常的顺从该会是恰切的历史事件,我们也会不得不探究其原因。只是,很难做到把诸多情节累加起来并且将其整体化:或者尼禄是我们的主角,他只要是说“卫兵,听我的”就足够了,或者卫兵们是主角,我们则将书写另一出悲剧;在历史中如同在戏剧里,一切都得到表现是不可能的,不是因为这可能需要太多篇幅,而是因为并不存在历史的基本事实,历史事件的原子。如果我们不再从它们的情节中去看这些事件,我们就会被无限小的漩涡所吸入。考古学家对此深有了解:您发现了一处略有剥蚀的浅浮雕,它表现了一个场景,其意义您无法知晓;既然一个最好的照片也无法取代恰当的描述,于是您着手去描述它。但是,究竟应该提到哪些细节,哪些可以悄悄地放过?您无法说出,因为您不明白这场景中的人在做什么。但是,您预感到,某个在您眼中毫无意义的细节,会提供给比您更有才华的同行解读这一场景的钥匙:在一个像是圆柱体的末端这轻微的弯曲,您看作是棍子的,可能使他想到一条蛇;这的确是那个人认为的蛇,那个人因此是天才……那么,出于科学的兴趣,描述一切?您试试吧。
没有原子似的事实
不幸的是,即使我们拒绝把历史事件看作是一个去掉个人色彩的行为,即使我们不堵住自己的眼睛以便不看见它的意义,我们的痛苦也还没有达到极限:在这条路上,我们不会遇到更多事件的原子,而且我们将会被两种漩涡所吸入而不再只是一个。一个已经发生的事件,不管它是什么,都暗含着一个语境,既然它有某种意义;它与一个情节相关并且是它的一段插曲,或者更确切地说,它与数目无限的一系列情节相关;反过来,人们始终可以把一个事件切割成诸多更小的事件。什么将会是一个事件呢?德国军队在1940年对色当的突破?这实在是一个战略的、战术的、行政的、心理学等的情节。历史事实的原子难道是两方面军队中每个士兵的个体行为,一个一个地?理解一个人,一个单独的人,也是艰巨的劳动。或者,每个士兵的每一举止,他的每一步?然而,一步并不是一种凭借精巧的装置可以记录的时空上的行为:它有一个意义,一个士兵不像是普通人那样行走,他走正步,甚至走鹅步;腓特烈二世离我们不远,腓特烈威廉一世也一样……选择什么呢?哪一出戏剧该获得我们的优先眷顾?我们不可能谈论一切,更不能讲述在大街上所有相遇而过的行人的生活故事。

描述整个是不可能的,一切描述都是选择性的;历史学家从未测绘出叙述重要事件的地图,他能够做的顶多是增加几条穿越它的路线。差不多像是哈耶克(F.von Hayek)所写的那样,语言愚弄我们,它谈论法国大革命或是百年战争仿佛它们是天然的统一体,引导我们去相信,研究这些事件的第一步,一定是去搞明白它们像什么,就像人们听到谈论一块石头或是一个动物时所做的那样;研究的对象从来都不是某一特定时间和地点一切可观察现象的全部,而永远仅是其中被选择的某些方面;根据我们提出的问题,同样的时空情境可能包含相当数量的不同研究对象;哈耶克补充说,“根据这些问题,那些我们习惯上视为一个单一的历史事件,可能分解为多种知识的对象;在这一点上存在着一种混淆,它主要是由今天如此时髦的教条所导致,依据这一理论,任何历史知识必定是相对的,由我们的‘情境’决定,而且必定要随着时间的推进而改变;对历史知识相对性的论断所包含真相的核心是,历史学家在各种不同时刻会对不同对象感兴趣,而不是针对同一对象他们将坚持不同的观点”。我们补充说,如果同一个“事件”可能分布在好几个情节之间,与之相反,分属于异质范畴的材料——社会,政治,宗教……——能够组成同一个事件;这甚至是一种极为经常发生的情况:大多数的事件属于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意义上的“总体性社会事实”;说实话,总体性社会事实的理论想要说的,其实仅仅是,我们传统的范畴观念歪曲了现实。
说到这一点,一个小小的谜团出现在我头脑里:为什么历史对象的分解,历史中的客观性危机是如此经常性的问题,而人们极少谈论地理学对象的分解和地理学的主观性?还有“总体性的地理事实”?但是,很清楚,一个区域并不比一个事件更多客观存在;我们按照自己的意愿对它进行切割(某个地理学的汤因比可能会宣布,在地球上有四十三个或者一百一十九个“区域”,而且它们全部“应该视为哲学地等值”);它解体为地理学、气象预报学、植物学知识,等等,同样清楚的是,这个区域也将由我们选择对它提出的问题而生成:我们是否将给田野问题以重要性,而且提出来这一问题?有人说,一种文明,总是从它自己的价值观出发向历史提问,而且喜欢把自己的过去当作镜子;如果各种文明真的有这些存在的需求,并且它们在历史中使之得到满足,那么它们在地理学中将尤其会使之满足,因为地理学将允许它们在它们的现在中照见自己。于是,人们感到讶异,并未存在过某种地理主义,如同曾有过一个历史主义那样:难道一定要想象,地理学家比历史学家较少哲学头脑,或者是哲学家有较多历史头脑,而较少地理头脑?
讲述变异的全部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须选择;也不存在事件的一个特殊种类(比如,政治史)可能是大写的历史,因而非要我们选择不可。因此,与马鲁(Marrou)一致,说任何历史编纂学是主观的千真万确:历史课题的选择是自由的,全部历史问题都有权具有相等的价值;并不存在大写的历史,也没有更多“历史的意义”;事件的进程(被某个真正科学的历史火车头牵引)并不是在一条完全标注好的道路上前行。历史学家为了描述事件场而选择的路线,可以是自由选择的,而且所有的路线都同样地合情合理(尽管它们也许不一定同样有趣)。这就是说,事件现场的轮廓还是它原有的样子,可能采取同一条路线的两个历史学家将会以同样的方法观察这个现场,或者将会非常客观地讨论他们的不同意见。
事件场的结构
历史学家们叙述各种情节,这些情节与他们随心所欲地开辟,以穿越那块非常客观的事件场(它无限地可分,并不是由事件的原子组成)的许多路径同样多;没有任何一个历史学家描述这块场地的全体,因为必须选定一条路线,而不能到处穿越;这些路线之中任何一个都不是那个正确的,不是大写的历史。总之,事件场并不包括一些人们可以去参观而且可以叫做事件的风景:一个事件不是一种存在的东西,而是多种可能路线的交汇点。
让我们看一看被称为1914年战争的事件,或者我们宁愿定位再准确一些:它的军事行动和外交活动;这是一条与其他的路径同样有价值的路线。我们也可以更宽泛地观察,并且进入到毗邻的领域:军事的需要导致在经济生活中的国家干预,激发出政治和体制问题,改变了风俗习惯,增加了女护士和女工人的数量,从而根本改变了妇女的状况……我们因此就到了女性主义的路线上,而且可以在那里或远或近地走一段。某些路线很短就转向(战争对绘画的演变很少影响,如果没说错的话);同一个“事件”,对一个特定路线是深层的原因,对另一个路线,可能就是插曲或者细节。在事件的场域之中,所有这些联系都是完全客观的。那么,什么是那个叫做1914年战争的大事件呢?它将是由您自由地给予战争概念的幅度造成的:外交行动或是军事行动,或者,对它进行重新剪裁的大小不等的一部分路径。如果您的观察足够开阔,您的战争甚至将会是一个“总体性社会事实”。
历史事件不是一些事物,一些确定的客体,一些物质;它们是我们在现实中自由操作所得的剪切画,一种进程的集合体,在其中活动着也静止着相互作用的物质,人和事物。历史事件没有天然的统一性;人们不能如《菲德尔》的高级厨子那样,依据它们真实的关节把它们切开,因为它们并没有什么关节。它们可能很简单,但是这个真相直到上个世纪末都不为人所知,而它的发现引起了某种冲击;人们谈论主观主义,议论历史对象的瓦解。这种现象只能以直到19世纪为止非常注重叙述事件的历史编纂学的特点来解释,以它的视野的狭窄来解释;它曾有过一种重大的历史被神圣化,尤其是政治史;也曾有一些“公认的”的事件。非重大事件的历史是一种望远镜,在让人们注意到天空中超出古代天文学家认识的数以百万计星星的同时,也让我们明白,我们把布满星辰的天空划分为星座是主观的。
因此,历史事件不是以一把吉他或是一个带盖子的汤碗那样的物质实在性而存在。还必须加上,不管我们怎么说,它们的存在也不是像一个“实测平面图”那样;我们喜欢说,它们本身如一个立方体或一个金字塔那样存在:我们从未在同一时刻看到一个立方体的全部立面,我们从来只能有它的某一个不完整的视角;作为抵偿,我们能够增加这些视角。它们也许还同样地是这些事件:它们不可接近的真相会归并我们有关它们持有的数不清的观点,而这些观点统统都包含有关于它们的部分真相。事情完全不是如此;一个事件与实测平面图的相似是骗人的,甚至更危险,而不是更合适。
(文本摘自保罗·韦纳著《人如何书写历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4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