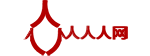打捞人物微表情 回望地方大历史

何光渝

《贵州人文精神读本》书封

《山高人为峰》书封
何光渝先生自2005年提出“构建地方文化知识谱系”这一文化命题后,他本人此前此后“讲好贵州故事”的著作,已经出版了二十部。
在其最新编著的《贵州人文精神读本》(以下简称“读本”)一书里,三十五位贵州先贤以及九种民间文献,用各自的“声部”自我“发声”,合唱着一首“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多声部”大歌。一曲歌成,贵州人“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的文化底蕴、性格气质、价值取向以及集体人格,尽在其中。
“要知贵州事,需懂贵州人”。在“读本”之前,何先生分别以创造贵州历史的“少数大人物”、“多数小人物”为观照中心,推出了《贵州社会六百年》、《铁血破晓:辛亥革命在贵州》、“贵州表情”系列之《如在天尽头》《山高人为峰》、《中国抗日战争全景录·贵州卷》等多部著作。“打捞人物微表情,回望地方大历史”,已成为他近年著述的“标准配置”。
何光渝先生说,他十分认同钱穆先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里的观点:“历史是人事的记录,必是先有了人才有历史的。……中国人一向以人物为历史中心。故要研究历史,首先要懂得人,尤其需要懂得少数的历史人物。”他说,“研读贵州历史,何尝不应如此!”只有直面生命的存在,把人当人看,才能秉持对过往历史的温情和敬意。
化繁为简:四十四张“面孔”勾勒贵州人文精神脉络
在“十三五”开局之年的2016年年初,“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的贵州人文精神得到提倡,也引来了社会各界的热议。“离开人,人文精神就没有落脚点。贵州人文精神的源头,就在历代贵州大人物、小人物乃至无名者的可贵言行之中。”在一次大规模的“贵州人文精神研讨会”上,应邀出席的文化学者何光渝先生作了如上描述。
当年五月,贵州人民出版社总编室负责人约请他,就“阐述贵州人文精神”的重大出版选题商谈。一向不愿苟同于“概念化、集体化写作”的何光渝,没有轻易“接招”。“概念化写作忽视人性,集体创作湮没个性。”他向出版方提出了一个“原则”:独立写作。征得出版方同意后,何光渝拿出了“原典说话,本义注释,个性解读”的写作体例和大纲。
不出三个月,《贵州人文精神读本》初稿成形……书稿完成送审后,中共贵州省委书记陈敏尔专门为之作序。序言中的评价是:“‘读本’一书较为系统地梳理了贵州先贤对天人合一、知行合一进行阐发和实践的相关著述与资料,并配以译注、解读,用翔实的史料阐述了‘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的贵州人文精神内核和历史渊源,具有重要意义和参考价值。”
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贵州省文史馆馆长顾久通读书稿后,写下长篇导读。他说:“贵州史籍很多,其中涉及人文精神的材料何止千万?本读本由何光渝先生精选出其中三十五个人物的有关材料,再旁征博引,细细加以注解评说。于是,贵州古今杰出人物一一显现……更难得的是,何光渝先生还注目贵州少数民族同胞的可贵文献,精选其中九则……” 顾先生说:“这四十多则短文,几乎就是一本简明的《贵州思想史料》。”
将浩繁的贵州人文精神史料,化为简明的贵州人文精神脉络,需要的是“举重若轻”的工夫。何先生告诉记者,“读本”写来并不甚费力。因为“‘读本’的材料,是从自己多年的读书笔记、杂记中整理而来,有长年沉潜的工夫;直观呈现代表性历史人物的言行,用原典说话。我并不试图去阐释所谓‘形而上’的理论问题,而只是用平常心、以一己之见,解读我力所能及的内蕴而已。”
何先生的创作手法,有些类似于文学层面的“立象以尽意”。想起了他曾讲过的一个禅意故事:有一天,徒弟向师父问“道”。师父说:“你先把这盐放到水中,明天再来。”徒弟照办了。第二天,师父吩咐徒弟:“把昨天放到水中的盐拿来。”徒弟当然无法拿出盐来。师父说:“从这边尝水,它的味道如何?”徒弟说:“有盐味。”师父又说:“再从那边尝尝,味道如何?”徒弟说:“还是盐味。”师父说:“你再到水中去找找盐,然后来见我。”徒弟照办了,然后对师父说:“我看不到盐,只看到水。”师父说:“你看不到‘道’,但它已在其中。”
顾久先生从“读本”看到了这样的贵州人文精神之“象”:海通抉目明志,终成伟业;申祐临危勇进,代君殉难;高庭瑶重德爱民,刑德交用;丁宝桢志在君民,实心任事;李端棻爱国无私,革新变法;阮则文泣告国人,以命殉邦;邓恩铭不慕名利,立党为公……九则民间文献:有的阐明万物一体,天下一家;有的彰明自然法规,追求和谐;有的保护生态,一丝不苟;有的明规设约,神圣严明……
出奇出新:秉持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
“我十来年出版的著作,立意、主旨、题材及内容,全都与贵州有关或很有关。”这些年来,“乡情独浩然”的何光渝先生,一直试图“在家乡这块邮票大小的地方,掘出一口深井”。支撑他往深处“掘井”的,是作为一个贵州学者的不满足感。
十八年前,他不满足于在中国文学史上,贵州文学仅仅是淡淡一笔甚至连一笔也没有的命运,仿佛这片土地上从未产生过文学,没有过文学历史的发生与演变。“但是,我们确实有过!”何光渝萌生了写一部贵州文学史的愿望和冲动。这就有了他著述的《20世纪贵州小说史》及主编的《20世纪贵州文学史》书系。贵州文学由此被“重新”发现。
他的这种“重新”发现的愿望和冲动,在过去的十多年间,由贵州文学扩展到贵州历史。“我不满足贵州史的书写现状。我自己有一些关于贵州人、贵州史的感与惑,但可能等不及其他人来书写和解读了。所以我就自己来寻求答案……”
在何先生的笔下,贵州历史上的大小“人物”们,纷纷再现于他们曾经生活过的那方人生舞台上,不再是“老脸谱”,多了些“新表情”。
“读本”里的郑珍,不是头顶“沙滩三贤”、“西南巨儒”光环的文化巨人,而是一个为母丁忧守墓的儿子。守墓期间,郑珍不断回忆起母亲生前的言谈举止,并逐一记录下来,不知不觉积累下六十八条,题名《母教录》,一个言传身教、教子有方、不盲目“三从四德”的母亲形象跃然纸上。这位伟大的母亲,不就是郑珍生命与精神的原点?
在《山高人为峰》里,陈夔龙不再是简单化的顽固派“封疆大吏”“前清遗老”,而是一个历经清咸丰、同治、光绪、宣统、民国近百年大变局,一直置身于大风浪、大漩涡之中的贵州人。这位士人也曾仕途得志,也曾先后尝尽亡国、亡女、亡妻这种“家国皆亡”的人间滋味。这样的陈夔龙,并不是“非黑非白”,而是杂色的。用何老师的话说:“陈夔龙人生得志,但不伟大;事业有成,却不圆满。正由此人在事业上不圆满,倒反把他那个真人显出来。”
与此同时,何先生让贵州史上一些“失语”“言轻”的“小人物”,发出了属于自己的最强音,成为“大写的人”。“读本”里的息烽人阮则文,一个弃官离职的无名芝麻官,文弱且患病。在日寇进犯的国难当头,上书当局呼请抗日,毫无回音。悲愤之余,自沉玄武湖,“尸谏”当局,举国震惊。一个文弱无名之士,践行儒家“文死谏,武死战”的文化传统,难能可贵,但极少为今天的贵州人知晓。
读何光渝的书,可以发现他对贵州历史的观点、论述,并非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而是事事有出处,人人有血肉。他的《贵州社会六百年》,是厚达七百七十多页、约九十余万字的大书,对六百多年来的贵州社会演进,有着十分精到的见解和剖析。但是,精彩的细节依然随处可见,以印证他的论述。例如,为了论证清代贵州社会家庭结构,何先生仔细爬疏了若干鲜为人见的史料,如“刑科题本”,这是地方督抚等大员向朝廷刑部报告各种命案的文书。何光渝从清乾隆四十七年至五十六年(1782——1791年)的刑科题本中,筛选出1303件与家庭结构有关的个案,从中发现有29个贵州的个案,通过细读、分析如普定县唐建发、贵州广顺州唐天成、印江县石建洪等案卷后,才得出清代中期贵州平民社会中家庭规模的判断,即:一二人的小家庭和十人左右的大家庭所占比例较小,五人左右的家庭规模应为主流形态,一般的变动范围在3——8人之间;平均家庭规模在4.5人左右。为了一个小小的结论,花费如此巨大严谨的工夫,在今天的学界已经十分稀缺。
何光渝先生对贵州史上的一些迷雾疑团、似是而非的结论,常有所考、有所言。“贵州”何由来?“普贵”是谁人?“矩州”何所在?……面对诸多悬疑,他像“侦探破案”一样,苦搜线索、证据,破除习见陈说,颠覆惯常思维,是他的追求。比如,人们通常会认为,在外来的文化迁客中,王阳明对黔地的影响最大。何先生则通过爬梳史料,认为明代贵州巡抚、一心“为祝全黔求太平”的江西泰和人郭子章,对贵州和贵州人的贡献也很大,很实在。再如今天被某些贵州人津津乐道的沈万三,何先生则以“明朝没有沈万三”为题,详述了斯人斯事的历史缘由、无中生有和荒诞不经。这种种自成一家的论点和表述,均见诸于何光渝的《如在天尽头》《山高人为峰》书中。
何先生说,他乐于以一个今人之心,去感受前人所遭遇的复杂环境、喜怒哀乐,以“同情之理解”去揣摩他们何以如此而不那般;如果可能的话,区别一下真实的和虚假的,确定的和不确定的,以及可疑的和不能接受的。
“直面生命的存在,把人当人看,秉持对历史的敬畏和温情。”正因为此,何先生得以在文史叙述上持续的出新与出奇。
对话
【 】
记者:您的所有著述都与贵州有关,感觉您在努力构建个性化的贵州文史叙事方式。想了解的是,您如何构建贵州文史叙事的内在路径与逻辑。
何光渝:当年提出“构建贵州地方文化知识谱系”,于我自然不是说说而已,只当看客,而是要身体力行。这种事,更需要“众人拾柴火焰高”。但各人的路径不同,我则只能量体裁衣。我自己的优势劣势,寸心自知:没有学历非“科班”出身、无师无门无宗无派“野狐禅”一个,是劣势;搞过多年文学创作文艺批评对汉语言文字感觉还不错,是优势。二者结合,文史不分家,一路写下来,就成了今天呈现于读者面前的这副样子。好在有读者不喜,也有人喜欢,这就够了。说实话,我并没有刻意去追求什么“个性化”的叙事方式。我的大多数作品,文字风格大体上就是我这个人日常说话的风格,顶多会书面化一些,但总会是真诚的、坦率的、不加掩饰的。心向往之的是“文如其人”。
对历史、特别是贵州历史的讲述,我其实也没有什么规划、计划之类,但大体上应该是我自己感兴趣的人和事,不一定是军国大事,但必须是有意味、有故事、有细节的,或是可以通过挖掘、发现出什么来的人和事。我已经出版了《如在天尽头》和《山高人为峰》,还有正在写作中的其三《往事犹可追》,其中所述的种种,都有这样的特质。出版社的编辑给它们冠以一个总题“贵州表情”系列,非常诗意,很合我心。表情总是生动的,无论美丑,都能给人留下印象,这就很好了。
记者:您的作品最不缺的就是“新”,细节的新、切入口的新、表达的新、观点的新。都说推陈出新难,但对您而言这似乎不是问题?为什么总能看到您对贵州人、贵州史的翻案与翻新呢?
何光渝:我从小就特别喜爱历史,特别是中国史。现在回想起来,其实就是因为能够从过往的历史中看到今天,看到未来。但读史时,有时又会读出陈旧甚至腐败之味。味从何来?我想,一是因为古之于今的不宜不适,前朝的种种事端,未必都能尽入今人的“法眼”,于是就“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二是历史书写的层层相因,辗转传抄,一段历史,早被从如数家珍说到发霉发烂;没有新的史料,没有新的史观,没有新的方法,没有新的表述,你还说它做甚?还有意思吗?无非拾人牙慧罢了!我不敢说自己的作品最不缺的是“新”,而只是企图说出一些自己的而非他人的读史心得而已。对贵州人、贵州史,我们比较清楚的是元、明、清、民国时代。但若上溯,不要说古史传说时代及夏商周,就连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辽西夏金……的确还有很多不清晰、不明了、不知道之处,亦如一根项链,“空白”“缺环”不是一般的多,根本就“串”不起来,很难成就一部完整可靠可信的贵州史。这真是若干代贵州人长时段的悲哀!现在我所能做和正在做着的,不过是九牛一毛而已,或许还是劳而无功。有首歌唱得好:“千百年之后,谁又还记得谁”呢?
记者:对您个人的经历,在贵州“讲好贵州故事”与“传播好贵州故事”,孰难?
何光渝:我想,就我们这一辈人的“责任与担当”而言,也许只能是尽自己之所能,把贵州的故事(主要是历史故事)讲得好一点,使之成为贵州的现实之鉴,并昭示贵州的未来。而把贵州的好故事“传播”出去,我的理解,更主要的,应该是各种传媒、机构乃至政府职能部门的“责任与担当”。如果有了好的内容好的故事,却传播不广、不远、不久,那么,“板子”该打谁?总不会打在说故事人的屁股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