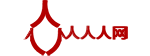刘文旋:布鲁尔与“强纲领”相对主义
原发信息:《哲学动态》第201810期
内容提要:在大卫·布鲁尔看来,相对主义是对绝对主义的拒斥,“强纲领”所为之辩护的相对主义,意味着科学中的知识主张不是也不能表示绝对知识。包括科学知识在内的所有知识都是猜测性的、有局限的,都是可以修正的,把“绝对”这个词语加于知识主张没有任何意义。因此,一个人接受或者信奉某种形式的相对主义,乃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关键词:布鲁尔/“强纲领”/相对主义/绝对主义
大卫·布鲁尔(David Bloor,1942-)是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简称SSK)爱丁堡学派(Edinburgh School)的首席理论家,也是SSK领域的领军人物之一,由他命名并阐述的“强纲领”(Strong Programme),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的科技研究(Science,Technology and Society,或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简称STS)产生了深远影响。SSK几经发展与演变,进入21世纪以后,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早已超越了当年的爱丁堡学派,“强纲领”也不再是学术研讨的中心议题。但是,由“强纲领”所引起的争论,比如关于相对主义的争论,则在后SSK时代继续存在,有时甚至要以“大战”名之。在经历了“文化转向”和“实践转向”,从“社会建构论”走向“实践建构论”之后,STS领域的相对主义色彩已是它最重要的标志之一。
相对主义也许是人类思维中最令人困惑的现象。尽管相对主义在人类思想史上绵延不绝、层出不穷,但历史上罕有以相对主义者自称的人,为之辩护者也是少之又少。然而,SSK中所包含的相对主义尽管广受诟病,仍被SSK的倡导者和同情者视为一项思想成就。究其原因,布鲁尔早在《相对主义、理性主义和知识社会学》①《三万英尺上空的相对主义》②《相对主义和知识社会学》③等文章中已经作出说明。但是,这些说明似乎并未得到人们的认可,质疑和反对仍然占据着意见的主流。中国学术界的情形大体类似。20多年来,在中国学术界对SSK有限的译介和研究中,对SSK相对主义的讨论,正如对相对主义本身的讨论一样,鲜有同情的理解。
在笔者看来,SSK确实对科学乃至一般地说对知识的性质提出了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见解,那么相对主义究竟在其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呢?为了更准确地理解这个问题,笔者在爱丁堡大学科学研究部(Science Studies Unit at the University of Edinburgh)访问期间,与该部荣休教授大卫·布鲁尔进行了数次学术交谈。本文的写作,就是在这几次谈话的基础上加工而成。这里的许多内容,尽管思想上与上述三篇文章并无不同,但是由谈话而来的表述形式和具体论说上的区别,使得它仍然能够自成体系,具有其自身的价值。因此,本文既可以看作是布鲁尔对他所持的“相对主义”的一种具体化解释,也可以看作是笔者对这种解释的理解和再解释。
一、“强纲领”相对主义
具身的情境感是人的重要感受之一,对于思想来说也是如此。例如有一次布鲁尔说,提到SSK,尤其是提到“强纲领”,绝大多数哲学家、科学家乃至科学社会学家,都会闻之色变:their faces get pink!(布鲁尔的原话,下同)在他们看来,这种理论简直就是邪恶的:it is evil!这种夸张的表达令笔者颇为惊讶:在西方的思想市场上,这个理论竟然是这样一种形象?关于“强纲领”的历史和理论,笔者此前并非一无所知,但是这种说法让笔者对它的生存环境有了一种新的认识。布鲁尔关于其来历的讲述,也使笔者得之于书本的知识更加生动具体了。
“强纲领”产生于爱丁堡大学科学研究部,这几乎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按照布鲁尔的说法,之所以有这么一个部,大约是出自生物学家瓦丁顿(C.H.Waddington)的提议。瓦丁顿认为,为了拓展未来科学从业者们的教育,应当为他们开设一门叫做“科学与社会”的课程。这项提议的背景是:20世纪60年代,英国正处于这样一个时期,政府明白科学的重要性在不断增长,科学家们的社会影响也相应地在日益加强,因此适当地拓宽科学教育,使之体现出与社会的更多联系,或许比过度的专业化教育更为重要。瓦丁顿建议爱丁堡大学建立一个部或者系,聘请一些科学家来专门开设这门课程。爱丁堡大学接受了瓦丁顿的建议,于1964年成立了科学研究部,并任命大卫·埃奇(David Edge)④负责这项工作。事后证明,这是一项明智而又影响深远的任命:埃奇是剑桥大学的射电天文学家,还曾经在BBC制作过一些科学广播节目;他与托马斯·库恩、玛丽·海斯(Mary Hesse)⑤和伊姆雷·拉卡托斯这些科学哲学家都很熟,事实上,他对哲学家们的熟悉程度,丝毫不亚于他对科学家们的熟悉程度。但更重要的也许是,他“选对了人”:布鲁尔、巴里·巴恩斯(Barry Barnes)和史蒂夫·夏平(Steve Shapin)这三位早期成员的加入,使得科学研究部很快就声名鹊起,成为STS的研究重镇。
大体来说,布鲁尔是科学哲学家,巴恩斯是科学社会学家,夏平则是科学史学家。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并没有现成的教学大纲,也不知道“科学与社会”这门课程到底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教学活动,因此他们只能从头做起。他们当时都很年轻,20来岁,获得了他们生平第一份工作,在小范围里给学习科学的学生授课,他们的任务,就是构思课程、为自己的课程写讲稿,并在教学当中摸索和实践“科学与社会”这门课程的设置意图。任职的初期,教学负担并不很重,他们之间因此有大量的时间进行交流。这种交流的成果之一,就是产生了“强纲领”。
由此,“强纲领”可以说是某种哲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相结合的产物。“强纲领”这个词巴恩斯和夏平都几乎不用,⑥只有布鲁尔用,因为这个词就是布鲁尔发明的。虽然如此,在基本观点上他们的意见是一致的。他们还幸运地分享着一种共同的潜在发展方向,因为他们三人碰巧有着相似的思想方式。他们都具备专业的科学背景,有着得自科学训练的思维习惯:巴恩斯以前是一名化学研究者,从事过核自旋共振方面的研究;夏平是一位生物学家,在遗传学方面做过工作,有一种高山苔藓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因为那是他的发现;布鲁尔的第一个学位是数学和哲学双料荣誉学士学位,随后在剑桥大学跟随玛丽·海斯研究科学哲学,不久又转到实验心理学,从事对认知的理解和分析。剑桥的心理学非常注重实际,布鲁尔受此影响很大。作为SSK爱丁堡学派的首席理论家,所有这些学术经历,都被他带入了上面所说的那种结合。
这种结合也许对SSK的发展产生了相当重要的影响。可以设想,一个历史学家、一个社会学家和一个哲学家,如果他们是反科学的,或者他们是人文主义者,更关注意义、解释而不是因果性,当他们把思想结合起来时,其结果可能会大相径庭。埃奇是一位训练有素的射电天文学家,他的思维方式从根本上说是科学的。当他接受任命的时候,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应该怎样做。他用心选择了他的成员,确定他们有共同的方向。结果证明是卓有成效的:知识社会学很快发展出了一种因果解释向度,这种向度被精练地概括为“强纲领”。然而,这种向度同时(在一些人看来很不幸)也是相对主义的。
历史上既有公开的相对主义,也有隐蔽的相对主义,“强纲领”是一种公开宣称的相对主义。所谓“强纲领”相对主义,也就是“强纲领”中所包含那种相对主义。“强纲领”是对SSK研究思路的一种严格的、原则性的规定。在《知识和社会意象》中,它的主要特征被布鲁尔归结为四个中心“信条(tenets)”:因果性(causality)、公平性(impartiality)、对称性(symmetry)和反身性(reflexivity)。意思是说,SSK应当遵循因果解释,这种解释应当关心那些导致信念或者知识表现为特定形态的(社会)原因;同时,它应当是公平的、不偏不倚的(impartial),即它既要解释真也要解释假,既要解释合理也要解释不合理;它还应当是对称的(symmetrical),即它要用同样的方式解释真与假,同样类型的原因,应当既能解释真实的信念,也能解释虚假的信念;最后,它的解释模式必须对社会学自身也是适当的,否则它便会不断地反驳自身。⑦公平性和对称性两条原则表达了SSK思路的基本要点:在所有信念都必须接受社会学因果解释的前提下,它把真(信念)与假(信念)、正确的(知识)与错误的(知识)和合理的(认识)与不合理的(认识),完全放在了对等的位置上,而不像传统观点那样,给真、正确和合理以社会学因果解释的豁免权。⑧这就是“强纲领”所表达的相对主义。在布鲁尔看来,它既是一种“社会学相对主义”,也是一种“方法论相对主义”。
布鲁尔对相对主义的态度相当坦诚,而且对相对主义的本质有着十分清晰的认识。在他看来,首先必须明确,任何类型的相对主义,其基本特征都是对绝对主义的拒斥。与相对主义相对立的概念,既不是唯物主义,也不是实在论,更不是客观性,而是绝对主义。相对主义与唯心主义也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因此在承认自己是一个相对主义者的同时,布鲁尔也认为自己是一个(休谟意义上的)经验主义者,以及(一般意义上的)唯物主义者。这并不矛盾,因为作为一个相对主义者只意味着,他认为科学中的知识主张不是也不能表示绝对知识。知识被绝对化,也便意味着它无条件地为真,它应当被深信不疑,被完全固定下来并且是永恒真理:正是这一类含义表示了“绝对”这个词的意义。相对主义者拒绝这些含义。因此相对主义者可以说:所有知识都是猜测性的,所有知识都是有局限的,所有知识都是可以修正的。科学理论总是会遇到某些崩溃点,科学理论几乎总是既有正确的东西,也有错误的东西。它们在某种近似程度上获得了正确的东西,甚至可能以很高的近似度获得了这些东西。这些说法意味着:把“绝对”这个词语加于知识主张没有任何意义,因此,或许可以说,一个人必须接受或信奉某种形式的相对主义。
但是在不同类型的相对主义中,也存在着拒斥绝对主义的愚蠢方式。比如,有人可能断定:“我们不知道任何事情,对吧?”或者说:“一切都只是意见,不是吗?”于是产生了一些浅薄的命题,比如:“对你来说那可能是真的,但对我来说不是。”不过,虽然存在着这类拒斥绝对知识的愚蠢方式,但仅仅拒绝承认知识是绝对的,并不必然导致任何这类见解。一个人可以既不承认知识的绝对性,又不陷入主观主义或与此类似的情形。作为一个相对主义者并不是必须认为“怎样都行”。布鲁尔肯定地说,与爱丁堡大学科学研究部联系在一起的相对主义不是这样的相对主义。“强纲领”相对主义是对知识绝对性所作的细致得多的形式化拒斥,它并不肯定或否定知识的真假,而是反对知识分析上的哲学优先性(philosophical a priorism)原则,并把它们置于同样的社会学分析之下。这种社会学相对主义拒绝主观主义的相对主义,拒绝反科学的相对主义,拒绝以高度个人化的知识概念为基础的相对主义。
反相对主义者认为,相对主义承认存在着若干认识世界的“同等有效”的方式,科学只是其中的一种。这种看法也许是对上述简单化的相对主义的一种正确描述,但它并不适合用来描述“强纲领”相对主义。按照布鲁尔的说法,这种看法并非来自爱丁堡学派,却被错误地转嫁给它了。“强纲领”相对主义表述了一种方法论步骤,用以确定真和假能够得到同等对待。在方法论上保持对真和假的同等好奇,并不意味着在认识论上承认它们“同等有效”,或者认为它们拥有同样的本体论地位。因此,“同等有效”这种描述完全是对对称命题的误解。其实,这个命题是建立在把信念区分为真和假这个假设之上的。一个人当然可以坚持一种与“同等有效”意思相同的对称概念,但是对称并不就是同等有效。这就像一个人可以坚持一种主观主义的相对主义,但是相对主义并不就是主观主义一样。所有主观主义都是相对主义,同等有效也可以是一种形式的对称,反之则不成立。实际上,对称命题的陈述形式暗示了它是否定“同等有效”论的,爱丁堡学派中也没有什么人支持“同等有效”这个论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