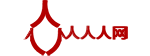龚琳娜:老锣拯救我于音乐迷途(组图)
(原标题:龚琳娜:老锣拯救我于音乐迷途(组图))

图书信息
书名:《走自己的路》
作者:龚琳娜 老锣
出版:现代出版社

“神曲侠侣”龚琳娜和老锣
一曲《忐忑》以神曲的姿态被无数网友传唱后,龚琳娜一直“坚定不移”地走神曲之路。这是龚琳娜与老锣这对原创音乐夫妻第一次开口讲述自己的故事。在此之前,龚琳娜也曾经历过假唱,经历过在音乐上没有方向的苦恼,是这场跨国之恋让她在音乐上实现了蜕变。
一
我认识老锣,是在2002年,一场名为“北京谈话”的音乐会上。我当时正在寻找新的音乐道路。
这是一场非常新鲜的音乐会,在当时的北京并不多见。我自己本来也是做音乐的,尽管我现在因为唱《忐忑》被大家熟知,但其实我是民族歌曲科班出身的,当时已经有些名气。那时我对自己将来的路怎么走陷入迷茫,所以就非常开放地去寻找所有新的东西。
那场音乐会后,我去了江苏连云港演出。唱的是那座城市的市歌,很多老百姓都会唱。舞台很大,观众很多,我穿得也很漂亮。但我不记得唱的是什么,歌是两三天前录好的,也不需要记歌词,现场放,对口型就好。我只需要现场表现得很美,穿着高跟鞋和漂亮衣服,真的是个表演,唱的是什么都不知道。
那天感觉特别长,仿佛那首歌老也唱不完,唱完后我跑回宾馆大哭。我觉得我再也不能这样了,非常痛苦。收入很好,接待也很好,宾馆也很好,一切都特别好,但我是“假”的。如果再这么假唱下去我肯定得抑郁症。
我非常痛苦地回到北京。一进家门,我妈告诉我常静打来了电话,说一个老外要跟我们做音乐。其实我心情非常不好,但是有新东西来了,我就马上放下包去常静那儿。到那时他们已经开始在做音乐了,三个人:常静、老锣和拉马头琴的张全胜。老锣和张全胜合作过,他们比较熟,也是很好的朋友。他们三个人比较有默契,可我不知道怎么做这样的音乐,完全加不进他们的即兴。
即兴完后,老锣让我给他唱首歌。我当时一片空白,不知道自己该唱什么歌。总不能唱《好日子》那些歌吧。从音乐学院出来的人,总觉得唱歌是很正经的事情,不会轻易唱;民间的歌手张嘴就唱,因为唱歌就是他们的生活。我们不是,当时我大脑就空白了。后来,我选了半天,才选了首贵州民歌《摘菜调》,很简单的,像首儿歌 。
二
老锣当时很想了解我们这样的音乐家,所以我们就又约了第二次即兴。这次我去了老锣住的地方,在左家庄附近的一个摄影棚。摄影棚没窗户,特别闷,但做音乐非常好。到时他已经准备好两个麦克,一个是我人声的麦克,一个是他的琴的麦克。我那时是在城市和尘世中特别焦躁的人,又很迷失,那摄影棚特别好,门一关,与世隔绝,特别安静。完全听不见汽车声,没有外面的光,觉得是另外的世界。前面坐着个老外,还是个陌生人,我也不了解他,只知道他是弹琴的。
老锣微微一笑,说:“你开始唱吧。”我又空白了。我说:“我唱什么?”他说:“随便。”我就在“随便”当中放松了,突然有了胆量,反正老外不知道我是谁,也不会戴有色眼镜看我,我的防范心就没了。我张嘴就唱,先唱了一段贵州彝族的《阿西里西》。唱完一段后,老锣的琴开始变换节奏,我开始唱第二首歌。一切都自然地开始,自然地结束。我知道怎么展开,他知道怎么推动。
后来我又唱了《月亮代表我的心》。我之前很少唱流行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唱了这首,就是很自然地唱了出来。我们在音乐上完全合拍,但我没意识到音乐的相合会把我们的命运牵连在一起。我们俩所以相爱,也是源自音乐。第一首是快乐的,第二首是感动和流泪,我哭了,我们特别和谐,第二个旋律完全是编的,自然地开始,自然地结束。我明白了为什么少数民族会用歌来谈恋爱。苗族的人或者像大理的白族,每年三月三的时候,那个节日所有人都会去,我不认识你,你也不认识我,但我们对上眼了,我们就会约好在一个地方唱歌,完全是在唱歌里面寻找爱的交流。
是老锣用这次即兴告诉了我一点:真实,不要有欺骗,不要有谎言。有史以来我第一次觉得唱歌是为了自己。我原来唱歌总是放着唱,一开始就是打开朝向观众的,那天是收着唱,是向着自己内心的,或者先朝向自己,再向外打开,状态特别好。而在此之前我从不知道声音还有方向。
那天我们俩一直唱了三个多小时,唱到天黑。在这三个小时里,我又哭又笑又唱又跳又叫,特别爽,还不累,就像经历了一次心理治疗。所以那次的即兴对我相当重要,我很感谢老锣录下来,可以让我辨析到当时的声音和心情,那次做完音乐后我的心已经向老锣敞开,只是我还没有意识到。
那后来我们又做了几次即兴,都录下音来。老锣回德国一个月后给我们寄了张CD,那CD里有半个多小时的音乐,不单是我的,也有常静的古筝、熊俊杰的扬琴、老锣的巴伐利亚琴,还有德国安德列的打击乐和马丁的键盘部分都录好了音,然后老锣剪辑出完整的歌曲。这对我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事。之前我做了个唱片《孔雀飞来》,花了不少钱、时间和精力。这事让我明白自己做一个唱片不是遥不可及的,只要你主动,去行动,马上可以实现。
老锣让我看到一个迅速的结果。我们跟他玩音乐的时候非常轻松,一个月后听到了中德音乐家共同合作的完整的音乐。即兴完以后,老锣说:“哇,你的变化非常大。”他夸我的声音拐弯之处很有韵味,细腻的同时又有很强大的张力。其实,这是我声音的本质。只是遇见老锣,才能让我的真实展露出来。
三
我们玩即兴时是4月初,老锣说7月初在德国有一个全世界最大的音乐节——TFF-Rudolstadt,他是这个音乐节的评委会主席。当时老锣就想邀请我去观摩这个音乐节。我太想去看看了!可我单独去德国,我妈肯定担心又紧张——那个老外把我绑架了怎么办?而且我英语不好,德语,更不会。有一次去贵州演出,张全胜也去,坐飞机我刚好坐他旁边。我问他:“我一人去德国行吗?”他说:“我可以告诉你,老锣是个好人,而且你去看看世界没坏处,反正你也不吃亏。”他们俩熟嘛,是很多年的朋友,他那么说,我心落地了。
可我妈那关还得过啊。那时候老锣住的地方条件不是很好,我就邀请老锣住我们家。我妈说不行。我后来就邀请他来我家吃饭,这个我妈是很欢迎的。那次是我妈和老锣的第一次见面,我妈也高兴,盛情款待,做了一桌贵州菜,两人也相谈甚欢。吃完饭的老节目是,我妈放我演出的VCD给朋友看,不管是谁来。这是她的骄傲。老锣没看过我以前的表演嘛,只和我即兴过。看完后老锣对我说:“我觉得好恶心,这不是你!”我不惊讶,因为我也这么觉得。我妈听了就跳起来了:“谁说我女儿不好,你知道她现在在中国多有名吗?”
老锣没有理我妈,而是跟我讲:“在这个电视里,我听不到我昨天跟你做即兴时那种最漂亮的声音。”凭他这几句话,我也想去德国,尽管我妈妈非常生气。我知道德国之行对我妈是件非常难接受的事情,但我父母有一点好,如果我特别坚持,他们不会怎么反对 。
四
从德国回来决定走新的路开始,我就一直在重新梳理自己:我为什么要唱歌,我和歌又是怎样的关系。 2002年我到贵州采风以后,当年10月份又去了浙江台州采风,去听南北民歌大擂台。那时我认识了歌唱家王昆老师,她跟我说过一句话:“你要附身于歌,或者是歌附于你的体。”当时还有周吉老师,他现在已经去世了,他是研究新疆音乐最好的专家。他对我说:“不要千人一声,你要一人千声。”
这些话我都记在本子里,但那个时候我并不能真正体会它们,只是朦胧地感觉到确实要学习更多更多的声音,要从民间出发。所以2003年4月份,“五行乐队”从德国演出回来以后,我又一个人去了福建采风。
这次是第三次一个人去采风,在福建的漳州地区,漳浦市,开始学歌仔戏,那里叫芗剧。我到他们的芗剧团,每天学。当时我认识了两个人,一个是老何,一个是小蔡。
老何是七十多岁的老头,他唱芗剧唱得特别有味,他教了我好多唱段,像《丢丢铜》、《卖药调》,这些都是他开始教我的,用闽南话唱。小蔡是拉四胡的,他特别年轻,比我还小。他作曲,拉胡琴,自己很向上。因为他经常给我拉琴,我来唱,老何来教,所以我跟他们俩成为很好的朋友,从早到晚在一起。我在那里待了一个星期,我走的时候他们都敲锣打鼓地送我走,他们都哭了。这几次的采风除了让我学到不同的歌和声音外,也让我体会到人与人的交心。因为我到那里,对他们来说是陌生人,但是我走的时候他们都流泪。没有防备之心,大家都是那么淳朴。所以我想,我去采风,让我明白如果要在唱歌方面提高自己,不是要去拜更高的教授,去学校里学什么,更多的要走入民间。在民间不只学到了唱法,也学到了怎么与人相处,怎么去面对所有新鲜的事。这几次的采风也让我开始有了自信心,所以后来唱电视剧《血色浪漫》里的歌就很好。虽然我并没有去过陕北,但是前面有过了采风的经历,唱《血色浪漫》里面很多陕北民歌的时候,我一下子就抓住了它直击灵魂的那种声音。
很多民歌只是唱法和味道不一样,但直击灵魂的那种方式却是一样的。而我们学东西,老要绕,比如说跳舞,要起个范儿才跳,为什么不直接跳呢。比如说古筝,把手提得老高才弹下去。其实民间的东西都很纯粹,“叭叭叭”就来了。所以我学到这些以后,有了后来比较自然的唱法。
但是我去学习其他声音的时候,我都不太意识到怎么用它们去唱新的作品。比如我唱陕北的民歌,我可以做到有这个味;我唱福建的,也可以这样。但如果用到新歌里面,就不会了,我抓不到,我不知道怎么融合。我想这也是原生态歌手或者戏曲人的一种问题,因为他长期就用一种方式,观念里也认为不可逾越。我真正开始将采风学习的各种声音融合起来,是在德国练歌的时候,就是我们“五行乐队”纽伦堡演出之前那段时间。
我从漳浦采风后,本来还要去泉州,想学福建南音,因为南音是最古老的汉族古乐。但是当时发生SARS了嘛,我就只能结束采风,回到北京。结果北京几乎所有人都躲家里了,街上没什么人。我当时就跟老锣商量,他说你来德国吧。因为他又联系了7月份在德国的演出。本来老锣是准备5月份来北京跟我们排练,那现在这样不行了,只能我去德国。所以5月底6月初我就飞德国去了。
五
在德国练歌的时候我被老锣严厉批评,老锣说:“你为什么能唱那么多戏曲和民歌,但是一唱新歌的时候,你就一种声,你只有一种声。”我说:“歌是歌,戏是戏嘛,是两回事。”他说:“为什么你不可以把唱戏的那种声音,只是用那个技巧放在新的作品里?”我说:“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戏和歌,就是两回事。”
然后他说:“我现在给你一个小时的时间,你就在屋里练,用一样的旋律给我出十种声音,一个小时以后我回来检查。”他把门一关,就出去了。
然后我就对着墙壁,大哭、大喊。因为我觉得这根本不可能!然后就哭,哭累了就试试吧。当时他给了我一段旋律,我就想,这次用小花旦,花旦的那种音色,可以。再用一次老旦,可以。再用一下秦腔里面的黑撒,就是黑头的唱法,哎?都可以啊!那几分钟我就通了!一下就通了,就转过来了。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意识到:天哪,那我们拥有的声音财富就太多了!原来我们在学校的时候总是听老师说,这唱法不科学,你的声音太白了,太直了。民歌直不直?那山歌,直溜溜地就出来了,你再给它卷起来,怪不得人家都说我们的民歌美声化。所以这一下就打破了我的审美,到底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该怎么唱,该怎么学。这就印证了周吉老师说的“你要一人千声”。但是反过来你不光一人千声,你还要把这千声融合起来,为你所用。所以我就觉得我找到宝贝了,因为中国那么大,东西南北,方言、民歌就不说了,再说戏曲,一个京剧里就有不同的行当,每个行当有不同的派,程砚秋和梅兰芳唱的都不一样,我学一辈子都学不完,我还迷信什么美声老师啊。
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意识到,我随时能找声音学。我就开始学评弹啊、学昆曲啊,研究它们的声音。比如说老锣新写一个作品,哎哟,我觉得这作品适合什么,我就去学那个,学了马上用。不行?不行再换一个。最后《忐忑》就这样出来的,所以《忐忑》有很多变化的声音,不是我生搬硬套地给它放上去的,都是有来处的,是我真正地融汇了各种唱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