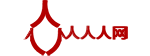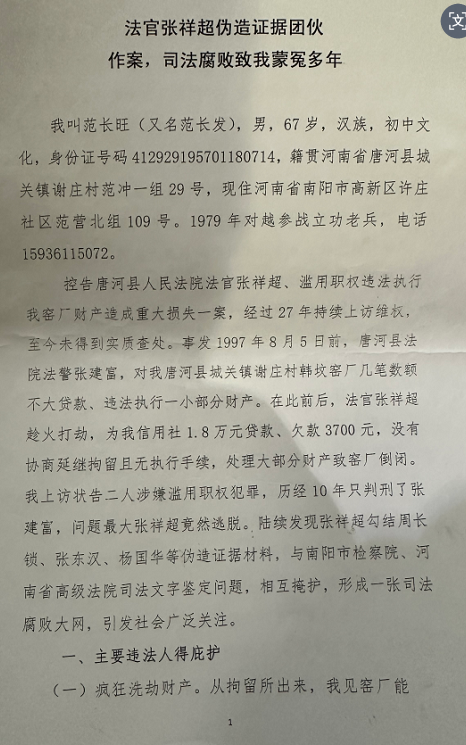科研资助如何“助产”原创成果
科研资助如何“助产”原创成果

“在科技创新中,我们选择的很多科技项目都是国外已经做过的,我们习惯于拒绝支持有争议的项目,排斥没有国外先例的研究,以及单纯追求研究论文数量等,这实际上就是对自己科研能力的不自信。”
■本报记者 王之康
最近,2019年诺贝尔奖的公布无疑是全世界最为关注的事。在过去一个多世纪的历程中,仅有少数科学家在青年时期就摘得诺贝尔奖的科学桂冠,多数诺奖得主在其科研生涯的中后期才抵达这一科学高峰。
众所周知,诺奖得主背后除了强大的科研团队,往往还需要庞大的项目支撑,可以说,科研资助对于科学家是否能够取得创新性研究成果甚至获得诺奖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那么,什么样的资助方式最有利于产生原创性成果?原创性成果如何才能更好、更快地被人们所认可?
长期资助与短期资助
从资助周期来看,有长期资助和短期资助之分。在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沈文钦看来,“长期稳定的资助,更有利于产出高质量研究成果”。
以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为例,2014年,NIH开展项目资助方式改革探索,设立了代码为“R35”的新资助方式。
这种“R35资助机制”改变了传统的“指南发布—项目申报—立项评审—过程管理与考核”方式,先后在6个研究机构进行试点,主要为杰出研究者提供长期稳定且灵活的经费支持;研究者可快速应对新问题、抓住新机会,且不受预设研究目标的限制;减少了研究人员撰写资助申请和管理多个科研项目的时间;同时确保首席科学家有更多时间指导初级科学家。
从资助周期来看,申请通过后,科研人员可获得5~8年的资助。NIH一般要求在第5年进行中期考核,并依据评估结果决定是否给予非竞争性的延续资助。
“与短期资助相比,这种资助模式更有利于科学家长期稳定地开展前沿研究。”沈文钦指出,在这样的资助方式下,研究人员的创新性明显要比其他需要竞争经费的人强。
不过反观国内,长期资助却少之又少,因为谁都无法预测那些有风险的项目最终会不会产出创新性,甚至颠覆性成果。而且,评审人本身就处于原有的管理范式之中,稳妥成为大多数人的一致选择。所以,短期资助成为主流。
正如日本广岛大学教授黄福涛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所说的那样,在中国,无论是个人还是团队申请的课题,一般最长也就三四年。“但在科研探索过程中,资助周期仅仅三年或四年是远远不够的,尤其是还想产出原创性、颠覆性的成果。”
传统的项目资助方式,因其周期较短、流程较多等特点,给科研人员带来忙于项目申报、研究缺乏连续性、无法适应当前技术快速变化等难题。可以说,我国难以产生具有颠覆性的原创成果,甚至更直白地说,难以获得自然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与此不无关系。
资助周期与资助目的
颠覆性原创成果的产出与资助周期有一定的相关性,但在黄福涛看来,与其讨论资助周期的长短,不如换个思路,即探讨科研资助的目的。
“现在,我们的很多课题是对已有研究的注解、论证,这一点在人文社科方面表现得尤为显著,在自然科学领域略好一些。”黄福涛说,应该在长期大局上做文章,无论是人文社科还是自然科学,或者其他交叉学科,国家层面只从资助目的考虑设立课题,专门用以作探索性、原创性、颠覆性的研究。“当然,这样的课题也要有一定资助年限,但不宜过短,比如第一期资助五年到七年,第二期资助十年到十四年。不管怎样,要想取得原创性成果,无论是资助团队还是个人,我们需要这种持续性的科研资助。”
在他看来,一个从零起步的人文社科类学科,一般情况下如果做不到十年,便很难产出像样的成果;自然科学可能会短一点,但也要有一个长期的积累过程。
无论是跟日本相比还是跟西方国家相比,我国都有自己的特殊性,因为1958年至1976年这段时间,除了航天、军工等一些特殊学科,基本上很多学科与外界(尤其是西方国家)是隔绝的。
“我们的科研工作要为国家建设服务,其中存在一定的历史惯性,有一定的历史原因。”黄福涛认为,中国发展至今天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想在国际上争创一流,就必须把目标放在全球层面,科研不能只谈解决中国问题、为中国现代化服务、为实现中国梦服务,更要为国际服务。“更直白地说,如果只扎根中国大地、解决中国问题,又想获得国际上的诺贝尔奖,本身就存在逻辑矛盾。”
一个很好的例证就是,2015年10月5日,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宣布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屠呦呦与另外两名科学家,以表彰他们在寄生虫疾病治疗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屠呦呦之所以能获得这一荣誉,是因为她发现了青蒿素,为世界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抗疟药。以青蒿素为基础的联合疗法(ACT)是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疟疾治疗最佳疗法,挽救了全球数百万人的生命。换句话说,屠呦呦的研究是具有全球性、公益性的。
除此之外,黄福涛认为,像这样的课题,应该多给40岁左右的中青年科学家参与申报的资格,不能只考虑资历,让具有一定头衔的学者独享。
老学科与新学科
中国科学院院士、科技部原部长徐冠华曾指出,我国存在着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和再创新不足的严重问题,这造就了一种文化,“在科技创新中,我们选择的很多科技项目都是国外已经做过的,我们习惯于拒绝支持有争议的项目,排斥没有国外先例的研究,以及单纯追求研究论文数量等,这实际上就是对自己科研能力的不自信”。
反映在科研资助上,就是大部分资源都配置给了老学科,而新学科获得的资源较少。
对此,黄福涛认为,这首先与我国国情有关。
中国的科学发展有其显著特色,从“双一流”建设学科来看,自然科学领域多集中在航天、农业、工程、生命科学等,人文社科领域则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等。“这些学科是短期可以看到建设效果的,这与我国国情紧密相连。所以,在这个大前提下,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一些传统的老学科容易拿到科研资助。”
同时,更严重的问题是,我国科研资助是有倾向性的,与普通学者相比,国内一流学者以其资历、社会影响力和学术影响力,在获取资源时具有更大的可能性。
“这两方面就造成了老学科,比如工程、化学、机械、农业等中国长期以来主要发展的学科,以及具有资历的老学者更容易获得科研资助,而年轻人很难获得资源,甚至他们很难发现国际上哪些是主流学科,哪些是有发展潜力的新学科。”黄福涛说。
在他看来,要解决这一问题,促进新学科的发展,首先要加大对40岁左右的中青年学者的科研资助力度;同时,国内学者一定要和国际上最杰出的学者、学术共同体保持联系;第三,要由国家出资,继续把大量年轻学者派到国外最好的学校、研究机构做合作研究,特别是从博士生开始,建立这种跟国际上的学术联系。
“还有一点尤其重要,就是大学一定要与研究机构以及企业的研发系统加强联系。我们要产生原创性的成果,无中生有,就要把握市场需求、科研需求。”黄福涛说,在日本,至少有三位自然科学领域的诺奖得主是来自于企业的,与大学、研究机构相比,企业对市场和科研需求更加敏感。
原创成果与科学规律
不过,让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刘益东更加关注的,是科研资助或自由研究产生的原创成果如何才能更快地得到科学共同体的承认,实际上,这是更加紧迫而且可以立竿见影的事情。
在他看来,原创成果的完成需要三个环节,即做出来、正式发表和得到承认,三者缺一不可。但事实一再证明,一项原创成果产生并得到科学共同体的承认往往不是一帆风顺的。
比如,1982年,以色列科学家丹·谢赫特曼发现了铝锰合金的准晶相,提出准晶体概念,并于2011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他提出新概念之后,遭受到科学界的大量批评,包括两获诺奖的莱纳斯·鲍林的公开质疑:“世界上没有准晶体,只有准科学家。”从1984年到1994年,鲍林质疑了十年,至死都不相信准晶体的存在。
“谢赫特曼的这一重大原创成果,在提出之后的十几年时间里并不被认为是原创成果,而被认为只是一个错误工作,这种现象在科技史上并不少见。”刘益东指出,“而且,我国学术界在承认自己同胞的原创成果方面似乎并不积极。”
正如中国科学院院士陆大道所说,一些人才和成果,在各种评奖的关口被那些热衷SCI的权威以一两个量化指标不够或由于没有外国人的好评等而被否定了、封杀了。
而这一现状,是我们应该极力扭转的。
《中国科学报》 (2019-10-16 第1版 要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