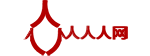访谈︱沈卫荣:从蒙元史到藏学研究
【编者按】2017年9月4日,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教授、长江学者沈卫荣先生在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作题为“我看新清史的热闹和门道”的讲座。借此机会,澎湃新闻特约四川大学鸣沙丝路学社任柏宗对沈卫荣教授进行了采访,谈谈他的治学经历。(访谈经沈卫荣教授审定)

澎湃新闻:我们知道,您在南京大学读本科和硕士研究生期间发表的毕业论文都是与蒙元史有关的。您最早对于蒙元史的兴趣是如何产生的呢?您现在以藏学为主的学术研究方向又是何时确立的?
沈卫荣:你提的这第一个问题,提到南京大学历史系元史研究室,就让我很有感慨。到现在为止,我依然认为南大元史室曾经是我学术生涯中的一个非常美好和非常重要的学术家园。可是,今天这个家园已经完全变样了,这里面有很多让人伤感的地方。实在难以想象,南京大学曾经有过的这样的一个传统优势专业,竟然就这么快地衰落了,这么具有优秀学术传统的南京大学,本来应该尽力维持和保护好这样一个优势专业的,真不知道这里面是哪里出了差错!让我感到伤感的另一个原因是我的导师陈得芝教授身体状况目前非常不好,陈老师在他那一代学者里面绝对是数一数二的顶尖学者。不仅是在蒙元史的领域里,可以说在整个中国古代史领域里,他都绝对是一流的学者。他不光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功底,而且对西方的学术背景也非常了解。他的外语水准也非常好,英文、日文、俄文、法文、德文都懂。陈老师在蒙元史学界里是有口皆碑的好学者,道德文章都受人称道,而且他到了80多岁高龄都继续发表很高质量的学术文章,对学术非常执着。可是,我一直不理解的是,南京大学历史系据说有好几位和他同龄的教授都当选了资深教授、学术名师等等,可像陈老师这样真正最资深、最优秀的教授却反而没有得到这样的待遇,实在是匪夷所思。不知道这样的学术等级评价在南京大学是怎么做出来的?陈老师自己对此觉得无所谓,但这样的事情对南大可不是无所谓的,南京大学的中国古代史研究何以不复往日的辉煌了呢?大家知道,南大元史研究室还有位刘迎胜教授,如果说陈得芝先生那一代学者中国内还有有数几位学者能与他比肩的话,那么刘迎胜教授在他这一代的学者中,他可真的就是更加难得了。他在蒙元史、中外关系史、丝绸之路研究、元代中亚史、历史语言学等很多领域中,他都有很高的造诣,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独步的,在国际、国内学术界也都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可是,最近听说他在南京大学历史系也没有当上资深教授,南京大学也已经让他退休了。我担心在他走后整个(蒙元史的)研究在南京大学难以为继了。他现在在清华大学国学院当讲座教授,清华大学很乐意接受他,北京的学生,如中国人民大学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学生们也都非常崇拜刘老师的学问,非常高兴可以有机会直接接受他的学术训练。我认为刘老师的离开对南大是一个非常大的损失。说起来,还有姚大力老师,他也曾是南大元史研究室出去的,现在在复旦大学,是复旦大学有数的几位文科资深教授之一,想想要是他还继续留在南大的话,现在大概也早该退休了。说来很不好意思,我自己在回国到中国人民大学工作之前,也是一心想回母校南大工作的,我出国前就是留校的老师,但留洋十六年以后却再没有能回南大的缘分了,说实话当时我是非常沮丧的。如果我们这些人今天都还在南京大学历史系工作的话,那至少在学术上能为南京大学增加一些分量,至少元史研究室依然会是一个高水准的学术团体。可是,我和姚大力老师都没有能留在南大工作,南大历史系有不少年长的资深教授留任,可陈老师、刘迎胜却都没有获得这个殊荣,想起来让我觉得非常难以接受。一个卓越的学术团体建立起来很难很难,但垮起来却很快、很容易,真不知道南大的领导和同事们对元史研究室的衰落有何感想?
至于我当时为什么要到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学习,这可以说是一件很偶然的事情。为什么呢?我当时上本科的时候比较幼稚,读了四年书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想做什么,也没有找到自己真正喜欢的领域。当时我的“志向”是咱们系里哪一位老师的名气最大,我就报考哪一位老师的研究生。当时名气最大的当然是韩儒林先生,所以我就报考了韩先生的研究生。可是等我考上时,韩儒林先生不巧刚好过世了,因而我没有成为韩先生的学生,但是成为了陈得芝老师第一个独立带的硕士研究生。刘迎胜、姚大力等老师当时都是韩先生跟陈老师一起带的,我则是硕士和在职博士期间都是陈老师带的,这是我一生的荣幸。陈老师的道德文章,我觉得实在是不可多得的,他是我一生的榜样,而且当时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的学术氛围、学术水准,我觉得在国内那真的是数一数二的。后来我在国外去了很多地方学习,也没觉得那些学术机构就一定超越当时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的学术水准,所以对元史室今天的衰落我觉得万分痛心。

我报考韩先生的研究生完全是出于无知和鲁莽,考上后对于元史完全摸不着头脑,觉得元史这门学问门槛太高,老师们的水准也都太高,要找一个属于自己的学术方向非常困难。后来陈老师给我指了一条路,他说元史研究有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就是在利用藏文文献这一方面还大有潜力。所以,他建议我先去学藏文,随后再从这一角度研究元史。于是,我就开始学习藏文了。学了藏文之后,发现藏学研究的前景比蒙元史好像要广阔很多。也不是说研究藏学就更容易成功,而是说藏学研究在当时相对来说还是一个比较空白的领域,它的资料、文献很多,不像蒙元史,让我感觉似乎找个题目都不太容易。所以我觉得我若改为研究藏学的话,只要找到一个能做的题目或文本,我就能有属于自己的一个学术方向,这样我也就慢慢转到了藏学的领域。随后的很多年里,特别是在我出国留学之后,我跟蒙元史的联系就越来越少了,但到了最近十年,我又回到了利用藏文文献研究元代藏传佛教和西藏历史的研究中。我觉得我自己这些年所做的应该说对元史研究来讲,也是一个比较大的贡献。陈得芝老师以前也做元代西藏研究,他在这一领域内无论国内还是国外都可以说是很一流的学者。但他做的是政治史、制度史和地理研究,而我做的是文化史、宗教史的研究。应该说,我这些年在这个领域的成果也可算是部分地报答了陈老师对我的培育之恩吧。
澎湃新闻:我们知道您回国之前在海外生活多年,在西方学习、工作的这段时间给您留下了怎样的印象和体会?
沈卫荣:印象应该是非常多的。但是我在国外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长到我已经没有多少印象和感觉了。很多人出国访问一段时间,甚至只访问一两个星期,回来以后就可以写长篇大论的感受。但是我去的地方太多、待的时间太长,反而谈不上有多少感受了。我在德国前前后后待了十年,现在家又在美国,还在日本工作了三年,所以感想也无从说起。我刚回国时倒是给我留下了一个很深刻的印象。我离开中国是在1990年初,那时的中国基本上还是前现代的,2006年我回来时中国则已经是后现代的了。在这16年的时间里,我错过了中国飞速发展的现代化过程。当然,因为我错过了很多东西,所以刚回来时也有很多的不适应,慢慢地我想过去自己错过的东西还是可以弥补过来的。1990年我出国时,中国真还是一个在很多地方都显得落后和虚弱的国家,这也是西方人对我们的基本看法。我们到西方国家去留学的人的境遇,完全是落后国家的人到先进国家去的那种境遇。不光在学术上,在生活上的境遇也不好。我出国时国家给我带在身上的只有75美金,这在今天看来是不可能的事情。我出国前在南京大学领的讲师的工资是100元人民币左右,大概可以买30多瓶啤酒,我的德国导师的工资则是一万多马克,可以买一万多瓶啤酒,所以当时的差距是很大的。在学术上因为需要从语言这一关开始,所以这也是一个比较困难的过程。但到今天情况完全不一样了。以前在中国要读到国外学者的论文很难,但今天中国在网络这一块比西方还要发达,利用网络进行文章传递非常便捷。相对而言,出国留学的重要性要比过去弱多了。现在我在国内也能读到国外的那些书,国外的学者也经常到我们这儿来交流。当年我出国时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对西方完全是两眼一抹黑,不知道西方是怎么一回事。本以为自己有的一切问题到了西方就都解决了,实际上是一切问题到了西方才开始出现。到了西方后,有很多的不适应。对我而言,我在国外的十六年整个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我不断地努力去学一点新的东西,适应一些新的情况。原来我学历史,后来学与西藏、宗教有关的学问。从蒙元史和藏学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我在国外的学习主要是能力的加强,在学术的基本方法上则并没有太多的不适应。韩先生留下来的传统、陈老师教给我的东西和我在西方学习、研究时学到的基本方法是一致的。所以我更多的是吸收了许多新的东西,不但在加强藏语文和西文的能力上下了功夫,而且还在佛学、宗教学、语文学等领域内吸收了不少新的知识。

澎湃新闻:您当年应冯其庸先生的邀请回到国内担任人大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负责人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呢?从研究所创立至今,已过十年,您如何评价研究所十多年来的工作?
沈卫荣:这也与一个很偶然的机遇有关。我在日本工作结束后本来有两个选择,一是去北美找一个教职,另外就是回国。回国我当然首选南京大学,我当时也跟南大接触过,南京大学人事处的领导表示很欢迎我,因为我出国前本来就是南大的教师,但当时的(南大历史)系里的负责人似乎对我并不热心,我等了很长时间一直没有得到让我入职的通知,所以我没有能够成功地回到南京大学。当时我正考虑要不要再在日本待一年,或者直接回北美,当时我也还在申请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佛教学教职。但正好在这个时候,我收到了北京大学荣新江教授的一封信,他说他替冯其庸先生招聘我,希望我能回国到新成立的人大国学院去工作。当时我觉得很惊讶,为什么国学院会找我?因为我的专业和国学好像没有太大关系。后来才听说国学院要建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还得到了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批示,国家也会投入相当大的资金来建设这个研究所。之所以要在国学院建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个方面,冯先生有一个“大国学”的理念,认为国学不光是四书五经,不光是汉族的文化,也包括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化,广大的西域地区是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西域的文化、文明也应该是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方面是从整个国际学界来讲,中国的西域研究处在一个比较落后的状态,特别是语言的研究。中国在粟特文、吐火罗文、梵文、古藏文的研究上都比不上西方的学术,因而应该努力夺回失落的话语权。所以,冯先生希望能得到国家的支持,建立研究所,招聘世界上比较好的人才来弥补这些缺陷。后来听说,当时冯先生在国内做了些调研,希望寻找合适的人来组织这项工作。很荣幸荣新江先生推荐了我,所以冯先生就首肯了,让我来担任这个研究所的负责人。我当时也将信将疑地回国了,回国后很快见到了冯先生,他把这两个方面的原因和我说了,我们便一拍即合。
因为有了冯先生为我们谋得的较好的条件和基础,我们一开始的工作都是非常顺利的。我们得到了非常多的支持,不管是道义上的,还是资金、人员上的。我们把做蒙古学、满学的乌云毕力格教授从内蒙古大学请到了人大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把荣新江老师一位叫毕波的弟子招聘到研究所,并很快派她到英国学习粟特文,从法国聘请了做吐火罗语研究的日本学者荻原裕敏,还从台湾聘请了从事西夏研究的俄罗斯学者索罗宁,还聘请了从慕尼黑大学刚毕业的从事梵文、印度学研究的张丽香老师,再加上原新疆考古研究所所长王炳华教授自一开始就在西域所工作,后来又有新疆吐鲁番考古研究所的所长李肖教授加盟,一下子我们就形成了一个很好的团队。应该说讲中亚研究、西域研究,现在世界上都没有这样好的一个非常集中的团队。我们做的工作也是相当不错的,得到了国家重大社科项目的支持,我们也出版了《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和多种学术丛书以及其他著作,还建立了汉藏佛教研究中心,成为国际上第一家,也是最有成绩的汉藏佛学研究机构,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学生。所以,我们自己觉得我们一直做的都相当好。尽管最近有人员的调动、离开,但我们这个研究所到现在为止仍在国内和国际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我们从语文学的角度来研究西域各个地区、各个民族的历史、文献、宗教和文化,培养了一大批的学生。由于一开始人们常宣传说我们西域所是国学院的亮点、重点,所以我们吸引的好学生也特别多。这些学生跟我们学各种各样的语言,有的已经毕业了,还有很大一部分在国外学习,他们都是人大国学院培养出来的,以后将是中国西域研究的生力军。对于研究所未来的工作,我们也还在努力,尽管目前也面临一些问题,但我认为这些问题都是可以克服的。如果我们继续推进、继续努力的话,前途还是非常可观的。

澎湃新闻:您在《想象西藏》和文集《寻找香格里拉》中都谈到外界(不管是西方还是内地)对西藏的跨文化误读,您提到西方想象西藏背后所受的东方主义的影响,同时您还谈到了内部的东方主义的问题。您觉得作为一位研究西藏的学者,对于向公众展示一个真实的西藏具有怎样的责任?可以做什么样的工作?
沈卫荣:关于西方东方主义影响下的西藏形象,或者说关于想象西藏这一国际化的工程,我写了不少文章。但这应该说并不是我的主要工作,也不是我的专业,我的主要工作是用语文学的方法来研究西藏的历史、宗教。然而我在西方见到的误解西藏的事情实在太多了,特别是对西方人寻找“香格里拉”、想象西藏的印象太深刻,所以我对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也逐步进行了解。慢慢地,研究中西方想象西藏的过程(包括对当代汉人想象西藏,把西藏作为一个寄托自己精神的乌托邦的研究)似乎也成为了我的一个比较重要的研究领域。
实际上,内部的东方主义和东方主义本身是一回事。不管是“东方主义”还是“西方主义”,都是从各文化自身的立场、观念、需要出发去看待与自己不同的、他者的文化。差别在于,因为西方在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时代拥有的强势地位,西方的看法会非常严重地影响东方人,而东方对西方看法则对西方人而言缺乏更大的意义。我们对美国人、欧洲人同样有偏见,但这样的偏见并不作用于西方。内部的东方主义是由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的一些西方人类学家们提出来的,指的是汉族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偏见,比如许多人对云南少数民族“能歌善舞”的看法,实际上跟西方的东方主义有异曲同工之处。许多云南人也自我“东方化”,比如把中甸更名为香格里拉等等。内部的东方主义实际上就是按照别人的想象来设计自己,这一行为出于各种各样的目的,比如经济目的、文化目的或者是发展旅游的目的。如今汉人对西藏的想象也是内部的东方主义,不断地在影响西藏,使西藏的建设按照东方主义的设想来做,甚至前段时间微信上还有人在传说中央政府准备把整个青藏高原变成一个国家公园,这显然就是受了东方主义对西藏的想象的影响。
学者向公众展示一个真实的西藏负有怎样的责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以前美国密歇根大学有个教授,叫Donald Lopez,他写了一本叫《香格里拉的囚徒》(《Prisoners of Shangri-la》)的书。这本书出版以后引起了很多热爱西藏的人、西藏专家和西藏人的反感。不过这本书其实是写得非常好的,解构了西方人对西藏和藏传佛教的建构。但是反感这本书的人认为,这本书在解构西方对西藏的建构的同时,不但把洗澡的脏水泼出去了,而且也把婴儿也一起泼了出去,即把西藏文化也给解构了,因而有人质问说,看了这本书后还有谁会有兴趣再去了解西藏和藏传佛教呢?我现在也碰到了这样的问题。我经常在解构别人对西藏的想象和建构,但是同时我们怎样才能把一个真实的西藏告诉大家呢?萨义德自己对展现真实的东方实际上是抱着怀疑的态度的,他甚至说自己根本不想为一个真实的东方辩护,甚至认为根本就不存在一个真实的东方。这当然是矫枉过正了。不过,向公众展现一个真实的西藏确实是一件颇具挑战的事情。谁能保证我对西藏的看法就一定是正确的呢?我觉得西藏最大程度的对外开放对于让更多的人了解真实的西藏就是最好的办法,让人们自己去看看西藏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另外,我自己也在努力地做一些工作,比如对藏传密教的研究和解释。我从自己的专业出发,告诉大家不要误解藏传佛教的许多现象。下一步我的计划是做一本密教诠释学的书,现在关于“男女双修”之类的东西被传得神乎其神,但是这些东西到底是怎样的,其象征意义如何,大家并不清楚。我想我能做的正是这一方面做一些学术研究、普及和解释的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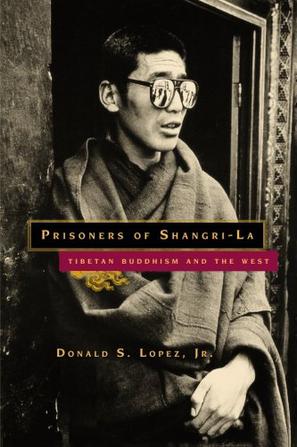
澎湃新闻: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人文学者的重要素养。从事与内亚、边疆有关的研究,往往更需要行万里路。您在读万卷书之余有哪些行万里路的经历?
沈卫荣:很遗憾,我不是一个喜欢行万里路的人,我在这方面做得很差。尽管我去过很多地方,但我更多的还是一个专注于文本的学者。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受我本人能力的限制,我最关心和最喜欢的事儿还是阅读文本,对实物的反应不敏感。国内、国外我也算去过不少地方了,西藏、新疆、内蒙等等,我当然都去过,也算“行万里路”了,但是这方面确实并非我的强项,“行万里路”并没有给我的学术带来一种根本性的推动。我不像冯其庸先生他们,他们做实地调查、研究都很厉害,很有成就,但是我更多的是从语文学的角度体验不同文字的文本之间的细微差别,这是我的强项。所以我并不是一个通过行万里路来帮助自己读万卷书的人。
澎湃新闻:不过您很推崇马丽华,她正是一个行万里路的人。
沈卫荣:是的。马丽华的故事确实曾给我带来过很大的触动。1990年代初的时候中国有些人膨胀的很厉害,老是在传季羡林先生“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说法,说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所以对自己汉族的文化特别推崇,觉得自己以后一定了不得了。但是,正好在这个时候,西方反而出现了另外一种社会现象。西方当时鼓励的是跨文化、跨宗教的对话,因为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们希望通过以传教的方式将他们的精神、理念传播给东方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或者说至少碰到了很大的困难了。再加上当时亨廷顿说“今后世界的主要矛盾、冲突将不再是意识形态的矛盾,而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所以当时西方知识界就在倡导文化之间的和谐,以及跨文化的对话与理解。正好在这个时候我看到了马丽华的作品。她非常触动我的是,作为一个汉人,她希望踏遍西藏所有的地方,去了解西藏,揭开西藏神秘的面纱,真正尝试去了解西藏的文化、文明到底是什么样子。通过她读万卷书、走万里路的方式与把自己的经历、想法写出来,对于年轻人了解西藏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如何向公众展现一个真实的西藏,我觉得马丽华就做得非常好。我到现在都还在推荐我的学生们去读她的书,她现在也还在继续写这类书。更让我感动的是,她好像在《灵魂像风》的后记中写到了这样一件事情。她说她自己这么多年在西藏,有时候感觉跟西藏的文化很近,有时候又感觉很远。对于不是自己本民族的文化,我们经常也会有这样的感受。人们花了那么多时间去了解西藏文化,有的东西了解了便不再觉得神秘了,此后也就不觉得很特别了。有的东西则始终感觉离得很远,感觉无法进入他者文化的精髓。马丽华讲了一个故事,说当她有一次做完了一段考察之后,正坐车返回,途中突然遇到一阵狂风暴雨,便只能停下车来避雨。待雨过天晴时,她看到道路前方有一群藏族同胞正在路上走着。她便想起刚才狂风暴雨时他们在哪里,他们是否淋到了雨。她觉得自己不仅没法跟藏族同胞风雨同舟,甚至也没法在下雨时请他们来车上暂避风雨,自己又怎么能说真正了解他们了呢?这就是马丽华打动我的地方。她对他者文化抱有一种正确的态度,也有一种情怀,没有大汉族主义的偏见。同时,外界的人以为马丽华在西藏待了20多年,应该非常了解西藏了,可实际上马丽华却并不认为自己对西藏的了解已经非常透彻了。这是一种虚怀若谷的态度。
澎湃新闻:现在“内亚”这个概念很火,包括您关于“新清史”的讲座也与此有关,您认为关于内亚的不同学科(如藏学、蒙古学、突厥学)之间具有怎样的内在关系?另外,与内亚有关的“不古不今、不中不西”之学过去少有人问津,而今则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您怎样看待这一现象?
沈卫荣:内亚这个概念实际上到现在也没有一个能让大家都能接受的界定。以前的“内亚”概念好像只是为方便学术研究而进行的界定,德国人过去使用的内亚概念基本上等同于中亚,中亚研究的主要内容就是研究蒙古、西藏、满洲和部分维吾尔地区。但是也有不同的界定方式,Denis Sinor先生好像写过一篇叫《Inner Asia》的文章,就是介绍什么是Inner Asia。但是,今天所说的内亚更多的并不是一个学术的词汇,而是将它作为一个地缘政治的词汇,跟学术并不是一回事儿。所以我觉得到现在为止,新清史也没有讲明内亚和内亚的性质究竟是什么,所谓Inner Asian Dimension到底是怎样的。我们从做学术研究的角度说,应当对其做更清楚的界定。内亚跟中亚、欧亚或者跟我们所讲的西域研究都有关系,实际上很多时候各自的研究范围都是重合的,只不过用了不同的表述方法。
为什么内亚或西域研究重要?因为这一地区处于中西之间,与现在提倡的丝绸之路研究关系密切。所谓“不古不今、不中不西”,实际上是“亦古亦今、亦中亦西”。西域既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也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所以这里是民族的熔炉、文化的熔炉,具有特别的意义。为什么当年有很多出国留学的中国学者都愿意学这个东西?陈寅恪提“不古不今、不中不西”时是非常骄傲的,他觉得如果一个中国人到国外去学汉学就很没意义,因为纯粹汉学的东西中国人往往比西方人更了解,而纯粹学西学,对中国人而言不一定有很大的意义,而且中国人学西方也仅仅限于学习,很难与西方形成对话。而与西域有关的学问,即“不古不今、不中不西”之学,正好可以使中国人与西方人在学术上做一番比拼。同时,这一块的东西以前中国懂的人很少,但它对研究中国的边疆又具有很大的意义。因而,当时涌现了像陈寅恪先生、韩儒林先生、季羡林先生等这样的一批人。季羡林先生留学时讲得就很明确,自己连辅修都不学汉学,而要学斯拉夫学、印度学等。从专业来讲,“不古不今、不中不西”之学属于中亚语文学,我们从来都认为伯希和是世界最厉害的汉学家,可是他实际是中亚语文学的教授。当然,他的汉学也非常厉害,可他不是去研究中国的四书五经、风花雪月,而是研究“不古不今、不中不西”之学。没有伯希和的语言能力,和他用语文学的方法研究中国古代文献,很多东西中国人是看不懂的。中国古籍中出现的很多有关西域名物制度的词汇,钱大昕看不懂,伯希和却能懂,就因为他对西域的胡语文字、文献很熟悉,而且还知道古代音韵变化的规律,所以他知道汉人自己不认识的那些词汇的来历原来是怎样的。正因为他能研究中西之间的各种学问,所以,伯希和的学术地位非常高。中亚语文学过去在欧洲、美国的地位非常高,可是后来都渐渐被人忘记了。现在人们知道伯希和很厉害,但却不知道伯希和是研究什么的。人们都说陈寅恪、王国维是国学大师,实际上并不知道他们是研究什么的,都以为《柳如是别传》、《人间词话》才是两位大师的代表作。实际上这根本不是他们主要的学术研究,他们主要的学术研究恰恰是“不古不今、不中不西”之学。

澎湃新闻:您认为对于有志于学习“不古不今、不中不西”之学的本科学子而言,需要在本科阶段做何种准备?您有怎样的学习建议?
沈卫荣:中国的教学有一个固定的范围,比如大家刚进本科,就会被设定为不同专业的学生。我觉得在本科阶段,一定要在广泛了解各个学科的基础上培养自己对某个专业的兴趣。任何想在学术上成功的人,一定要把学术与自身兴趣联系在一起。只有有了兴趣,你才能扎进学术中去,才能专心投入。中国很多人都喜欢吹牛说自己读过这本书,读过那本书,可是他们读了这么多书有什么用呢?好像都是为别人读的,而不是自己真正需要读的。真正需要读的书就是你对这些书真正有兴趣了,真正扎进去了,这样你读书时对这些书才真正会有反应。如果是泛泛地随大流,读很多书,那是没有意义的。不是你读什么书,而是你如何读书,对你成为什么样的一个人最为重要。另一方面,因为我是推崇语文学的,所以我认为一定要打好语文的功夫。汉语的功夫肯定要打好,若有志于学“不古不今、不中不西”之学,外语也一定要打好。学好这些语言后,你要是想在此基础上做研究,这就方便很多了。有的同学接触与边疆有关的内容较早,逐步产生了兴趣,这个时候就一定要打下语言的基础。日本学佛教的人一进入专业便开始学梵文、藏文,可是中国很多学生到了考博士的时候才说自己想研究佛教了,要学梵文了,可是到这个时候才学实际上已经太晚了。要是想研究西藏、蒙古,也是一个道理。所以我觉得在本科期间,首先要把兴趣放开,确定了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后,就要打好语文的功夫,并学会扎实的、实证的学术方法。这些东西学好了之后干什么都行,而如果没有学好的话,以后做啥就都很困难了。